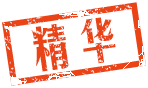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1500粤星月 于 2017-5-19 12:25 编辑
这是您唯一的一次乘车 母亲 您躺在车肚子里,像一根火柴一样安详
一生 走在地上的母亲 一生 背着岁月挪转的母亲,第一次乘车去旅行 第一次享受着软卧 平静的躺着像一根火柴 只不过 火柴的头黑,您的头白
这是您第一次远行 就像没出过门的粮食 往常,去磨坊变成面粉的时候 才能够登上您拉动的老平板专列
母亲 我和姐姐弟弟妹妹陪着您远行 窗外风光一闪而过 母亲 您抬头看一看,你怎么躺着像一根火柴一样
终点站要到了 车外是高高的烟囱
这是最近刚刚火了一把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工厂工会主席郑西坡为自己死去的母亲所作的一首诗,题目叫《母亲的专列》。当我听郑西坡朗诵这首诗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我母亲的身影!朗诵还没完,我已感动到泪奔!是的,我母亲也像一粒粮食、像一根火柴那样安详地躺在她的“专列”上,由爸爸和我们兄弟姐妹一起护送——即便是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一天、那一刻!
我的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家妇女,生于1936年,殁于1987年。没上过一天学,只会写自己的两个名字——为何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闺名,父母起的;一个是官名,丈夫(也就是我爸爸)起的。母亲姓尚,爸爸给取的名字叫尚淑慧。爸爸是个教书先生,给妈妈取名自然有深意。而妈妈,也真的就是妇从夫命,一辈子唯爸爸的命令是从,上敬公婆和兄嫂,下与叔叔和婶娘们和睦相处,还要额外关爱五叔家从小失去母爱的三个儿子。从家里到村里,母亲一辈子都是好口碑;从言语到行为,都恪守贤淑与善良,阐释着要淑慧的夫命。
可是,在那样缺衣少食的年代、在那样几十口人的大家庭里,赢得好口碑得受多少委屈、甚至是屈辱,只有母亲心里最清楚。更何况,妈妈嫁给爸爸之后,十年生了三个女儿,被人讥讽说生不出儿子,被爷爷奶奶嫌弃了十几年!直到结婚第11年生了我哥哥,这种无后为大、戴罪忍辱的日子才算告一段落。后来,明明长得虎头虎脑的哥哥,时不时总会闹一些小毛病,妈妈心里那个担惊受怕呀……于是在院子里种下一棵苹果树祈福之外,不得不接着生孩子,于是,我比哥哥晚五年出生,因我又是女孩,妈妈只好再生,于是有了小我三岁的我弟弟。生弟弟那年,妈妈已经四十岁,大姐都高中毕业了!因为是高龄产妇,妈妈患上了严重的妊娠高血压,生产时病情特别危重,爸爸和大姐的心思都在妈妈身上,弟弟平安,便被搁置一边。再说,那时候孩子多,也不给孩子过生日,也没人在意这孩子是哪天生的。于是,弟弟虽是我们兄弟姐妹6个人当中唯一在县城医院里出生的,但也因此竟没人记得弟弟的生日,若是在农村生的,接生婆和左邻右舍,没准有人会记得呢。弟弟一直说妈妈记得他的生日,小时候吃过妈妈煮的生日蛋。可是,妈妈去世之后,彻底没人知道弟弟的生日了!
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摄于1976年)。摄影师是爸爸周末带回来专门为爷爷奶奶拍老人照的,顺便给爸爸和他的兄弟各家都拍了全家福。 对爸妈来说,有了两个儿子,已是心满意足,再也不要生孩子。可以照全家福了! 我家西房老屋门前初升的太阳,让大家都有点眯眯眼儿~
爸爸兄弟八个,妈妈进门时,八叔还是个小学生。只有一个姑姑,排行老二,据说姑姑5岁时就被头插草标卖给外乡人做童养媳了。还有四叔16岁时征兵入伍,支边去了新疆,后来在库尔勒安了家。隔几年省亲一回,除此之外,几乎与这个大家庭再无瓜葛。一大家几十口人,只有爸爸一个在外工作,其他人都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儿(俚语:在一个锅里吃饭)。这样的大家庭,人多口杂,没有爸爸在身边呵护,妈妈受委屈自然是少不了,但妈妈从来不向爸爸告状(妈妈去世后爸爸说的)。直到八叔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才按照爷爷奶奶的意思分家,大家庭分成八个小家,每个兄弟和妻小自成一家,爷爷奶奶跟小叔一家。因为爸爸有工作,所以自动选择一家人净身出户,连一根筷子、一样农具都没有拿。 按说,从此我家的日子能好过一点了。可是,让现在的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当年爸爸教书的那点点工资,分家后仍然不属于我们这个小家,而是由爷爷奶奶支配。比如,即便是两个伯伯的女儿都出嫁了,伯伯家里添置农具,还是找爷爷奶奶花爸爸的工资。相反,为三个姐姐上学,爸妈却没少被老人和兄弟妯娌们诟病,都说我爸妈是“拿钱打水漂”、“拿馍馍往沟里倒”,也就是白白糟蹋钱和粮食的意思。七十年代末,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很久,叔伯们家里急用钱,仍然找爸爸,虽说没有老人家在世时那么任性,也会说是借,但基本上等同于拿。爸爸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升职到县教育局做教学研究,他能有多少钱工资啊,哪经得起这么一大家人你借他也借?甚至暗地里夸耀谁借得多就是有本事!要说妈妈心里一点意见没有,那才是奇事怪事。爸爸很少在家,月月有工资在手,所以回家来看到的都是笑脸,听到的也是奉承话,哪里能体会妈妈累死累活时也没见谁主动出来帮扶一把的苦楚? 早些年的事情我也只能道听途说,但自我记事起,到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之前,我们家不仅缺吃,也缺穿。比如,我基本上没有穿过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我的小学毕业照上明显能看到肩头的大补丁!不过,那时候农村的孩子都穿的差不多,没人笑话,我也不以为意。而我最想知道的是:七婶、八婶那么年轻,她们为什么可以不去地里劳动,而我和弟弟却因为妈妈总要下地劳动而被妈妈锁在屋里哭天喊地没人应!那时候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一到寒假,拉肥上地,一到暑假就平整土地,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但也只有这两个假期,我们全家人能帮妈妈去挣工分,就连还没上学的我也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长大后才知,当时家里没有男劳力,姐姐们又在外上学,再加上女人干一天活只能挣9分,男人却能挣10-12分!妈妈没有队上男人们的工分高,偏偏家里这么多孩子,口粮全指望妈妈来挣。挣不够工分就分不够粮食,妈妈不拼命争取下地劳动怎么行?! 没粮没钱的日子到底有多艰难,我那时小,没有深刻体会,只记得经常和三姐偷偷剥花卷皮吃——那时候的花卷,可不是后来白面里还卷上油盐的那种软香的纯白面花卷,也不是如今玉米面里加糖加白面甚至加上红枣、葡萄干、干果的那种松软甜香发糕,而是金-银-卷!也就是一层小麦面加一层纯玉米面或高粱面再卷成卷,蒸熟了看就是白面卷着黄面或者红面,即所谓金银卷。听上去好听,吃起来又酸又涩又硬,我和姐偷吃的就是最外面那层小麦面。)如果家里还有小麦面粉蒸馒头,都是尽可能给县城里上学人吃,哪怕这馒头一点都不够白,但口感总是好过玉米面和高粱面。我那时候最盼望的事就是能快点去城里上学,那样就不吃或者少吃玉米面和高粱面了。
好长时间,我都不能理解周六爸爸从县城回来,晚上爸爸妈妈吹灯之后说悄悄话,说着说着,妈妈就会在被窝里啜泣(我们睡大炕,所以我和弟弟一直跟爸爸妈妈睡一起)。唯一一次可以称之为吵架,是因为爸爸向妈妈发了很大很大的火,弟弟吓得哇哇哭,以至于把哥哥姐姐们全都惊动了,一个个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后来我长大一些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那是八十年代初,我们那里农村也开始承包土地了!我家除了爸爸是公家人,我们兄弟姐妹和妈妈共七口人都有分到土地。生产队还分给我们家和七叔两家共有一头牛,可是没过多久,有一天七叔放牛时没用心,让牛吃了太多刚淋过雨的草,牛胀死了!两家十几口人的土地,没有一个大牲口耕地怎么行?!这一次,妈妈竟然自作主张,从邻村山庄上买了一头牛,不对,是两头牛回来!是母子俩!700块!这么贵,全村人都震惊了!七叔更是态度坚决地说:三嫂自己要买牛,跟我家没半点关系,我没钱,我不管!呵呵,生产队分的那头牛倒是跟他有关系呢,死了也就死了,他也不提承担什么责任。妈妈买的两头牛,母牛450元,小牛犊250元,卖方坚持必须一起买走!小牛贵是贵了,但妈妈就是看上那头母牛身强力壮,所以非买不可。好家伙!700快,几乎是爸爸两年的工资啊!在那个一分钱恨不得掰八瓣儿使用的贫穷年代,妈妈没跟爸爸商量就买了,而且还赊账!妈妈那时候嫁过来有二十年了吧,一直谨遵“淑慧”的本分,爸爸哪里见过妈妈这份胆量和倔强?!平日里再温和不过的爸爸,这一次面对妈妈,那是一个震惊和愤怒啊!奇怪的是妈妈面对爸爸的咆哮竟然没哭,爸爸不听,她就不解释,低眉顺眼任凭爸爸发火。
终究,这对在山里放养的“野牛”母子从此就在我家住下了,等小牛满一岁之后,套上鼻圈、拴上缰绳就卖了。据说卖到350元,牛钱就还掉一半。爸爸不生气了,还请匠人来给母牛盖了房子呢,借着我家西房的山墙,几乎和厨房一样高大,不仅宽敞,还很豪华——妈妈坚持在牛房里盘了一个小炕,冬天最冷的时候可以通过烧炕让屋里暖和起来,给牛母子取暖。每逢牛妈妈产崽时,我妈妈还一连几天住在牛房里昼夜伺候。爸爸妈妈把母牛当宝贝,可是却苦了我这个小屁孩!
山里放养的野牛,那真叫一个野啊!村里小伙伴放牛都是把缰绳往牛犄角上一盘,任由牛儿们悠闲自在去吃草,小伙伴们就可以自由撒欢儿了!可我家的母牛,她就是一个“悍妇”啊,我一个不留神,她就跟别的牛顶仗!而且力大无比。最惊险的一次是:我牵着它下坡去溪边饮水,迎面上来一头黑牛,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家母牛脑袋一摆,只一下,那黑牛就从坡上翻着跟头滚下去了,我和那个小牛倌吓得目瞪口呆!那年代,农民家里的牛,大部分都是砸锅卖铁买来的,比人还金贵。黑牛不会给摔死了吧?!伸着脖子等半天,直到黑牛自己挣扎着站起来!从此,我妈给我的命令就是必须抓紧牛缰绳,无论是出门饮水吃草,还是耕地拉车!唉!好不容易跑到野外,没有大人管束,我却被牛给牢牢拴住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玩!
不过,因为这头牛,我也有欢喜事儿——第二个牛崽崽卖掉之后,妈妈奖励我一双黑色高腰雨鞋!我心里那个美啊,恨不得天天下雨,可以穿上出门去得瑟!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奢侈到给孩子买雨鞋,大人雨天出门在泥水里走路也只是穿木屐——就是跟鞋子一样大小的四条腿的小马扎,用麻绳捆绑到脚上就行,雨地里行走的艰难可想而知。若没有十分要紧事,没人会在雨天出门。而我竟然有了一双雨鞋,还是高腰的,到小腿肚那么高,在村里的伙伴们中间,那绝对是蝎子那什么,独一份啊!
从八一年到八五年,母牛除了耕地,先后在我家生过两个牛宝宝,别人羡慕地流口水,因为妈妈不仅还清了买牛的款项,还攒钱给家里添老母猪。这老母猪跟母牛,就像要比赛似的,每年腊月和暑假这两个黄金时段里各有一窝小猪仔出生,只需一个月,每只猪仔就能卖8块钱。猪粪牛粪都是宝,就连猪圈牛圈里起出来的土,那都是上好的土肥,俺家粮食产量节节升。
现在有个流行语叫“羡慕嫉妒恨”,或者“羡慕嫉妒,不恨”。恨与不恨,我都体会到了。那时候村里人开始说我家一屋子女人,种地却是好手,就连养牛养猪也是如有神助。我们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确实感觉很是自豪,对妈妈的佩服那是打心眼里来的!我也不计较妈妈天天催促甚至是逼迫我放牛打猪草时我所流过的汗水和泪水了。可是,某一天,我家新生的才两个多月的小牛犊受伤了!明显是有人用钝器故意打的——小牛右后腿上部(也就是屁股)的那块平坦的俗称“锨板骨”的地方被人打烂了!妈妈接到村里一个小孩子的通知后匆匆过去,发现小牛卧在打麦场附近痛苦哀鸣,妈妈当时就哭了!我也哭了!因为小牛流血了,已经站立不起来,我和妈妈也抬不动它!这可怎么办呢?我真担心小牛会不会疼死?!以前去山里割草,路上遇到别村的人,听人家讲故事,说他们村有坏人用青草引诱牛或者马,然后镰刀一伸就把牛舌头马舌头给割掉了!我堂兄还笑话那人说:你们村里的人咋就那么坏?割了舌头,那还不把牛或者马给活活疼死、饿死?!…….谁知,竟有这样的厄运降临我家小牛身上?到底是谁呢?咋就这么狠心?两个月的小牛就像两岁的娃娃一样稚嫩招人喜爱,怎么就能下此毒手?!看着小牛的伤痛,看着妈妈的哭泣,我心里害怕的要死,真希望爸爸能从天而降!眼看着夜幕就要降临,风吹得我直打哆嗦!我们不能就一直这么守着小牛哭吧?可又能怎么办呢?妈妈忽然擦擦眼泪,对我说:你八叔应该下班回来了,赶紧去叫他来给小牛看看病。对呀,我八叔是乡上兽医站的兽医啊,他一定能治好小牛!我奔跑到八叔家,一看院里的自行车,就破涕为笑,拼命喊八叔。八婶出来说:你这娃,喊魂儿啊?还是见鬼了?!喊上八叔,我又去喊了五叔家的几个堂哥。夜幕下,一伙人齐心协力把小牛抬回家里的牛房,放在一堆干草上。那晚上,很多人围在我家牛房看八叔给小牛动手术。我不知道,有没有做了这伤天害理的事情的人也在人群中?这件事,是一桩悬案,一直悬在我心里。妈妈那天的哭声和眼泪,让我对人心、对人性的险恶和丑陋第一次有了深刻的记忆!
我八一年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大姐姐结束在乡里的劳动锻炼,当了民办教师,冬天就结婚了。二姐和三姐相继在县城上高中,住校;哥哥从小就跟着爸爸在外读书,都是周末才回来,所以,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妈妈和从前一样辛劳,整日没个空闲。忙了地里又忙家里的猪和牛,连我也算半个劳力,不是打猪草,就是漫山遍野给牛割草——似乎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大牲口了,以致于草不聊生!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定制”的小号背篓,天天一放学就跟着堂兄堂姐们往深山里跑,披星带月才回家。扒几口饭,又和妈妈铡草——夏天铡青草,冬天铡秸秆麦草。等到牛儿悠闲地反刍之时,我和妈妈也才安闲下来,在煤油灯下,我趴在炕沿上做作业,妈妈捻麻绳拉鞋底或者做鞋帮子或者缝补衣服。我常常就那么趴在炕沿上睡着了。醒来却是睡在炕上,总以为在做梦。只有周日和每年寒暑假是最热闹的,也是我最幸福的日子,爸爸回来了,兄弟姐妹也都回来了,我不用干活了!而且寒暑假似乎也比较农闲,来家里串门闲聊的人也是一波又一波,妈妈也不会抓我这个小壮丁了,可以疯玩一天或是整个暑假!往往暑假那时,村里乡里还有秦腔上演,亲戚们也会被邀请来住几天,那真是一段段农村人最欢乐的日子!
我妈妈还养过鸡、鸭、长毛兔和桑蚕。还记得春寒料峭时,一到傍晚,妈妈竟然会把装有鸡仔鸭仔的鸡笼鸭笼放在热炕上,就怕小鸡小鸭冻着,或者被老鼠咬死。十几只小鸡都开始有打鸣的了,笼子里不能关了,就在院里院外的散养,家家户户都这样嘛。谁知某一天,大伯扔了一包过期的老鼠药在大门外的粪堆上,我家一窝小鸡全完蛋;还有一次是村里闹鸡瘟,眼睁睁看着已经能飞上桃树的半大小鸡,一个一个蔫头耷脑地从树枝上掉下来死去,妈妈一直念叨“罪过!罪过!”至于小鸭,那真是我的罪过——我从池塘里拎回来一桶满是红虫子的水,然后把8只小鸭放进去吃虫子,本想着过一会儿就把小鸭捞出来,谁知三姐喊我去推磨。小鸭们被我遗忘了。结局就是水桶里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最后只剩下一只活的在哪儿悲鸣!从此,我家只养一两只母鸡,有鸡蛋吃即可。至于养蚕,二姐和三姐印象最深刻,一般每年春夏养两拨。每当想起,就觉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犹如在耳。蚕成长速度快,越到成熟前,吃得越多,一个个半立着身子,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即便是雷雨天,姐姐也必须去采桑叶,姐姐说从头到脚都在滴水,你想想背上的绿桑叶有多沉?她以后绝不养蚕。呵呵,我倒是记忆中欢喜更多一点,看着蚕成长,摸一摸很柔软光滑又冰凉,挺好玩;等到妈妈煮茧子拐丝线的时候又捞出蚕蛹给我吃,觉得很美味;再看妈妈给白丝染成五颜六色做端午香包给我和弟弟戴,心里别提有多美了!还有,妈妈教姐姐们拿花绷子绣花,在肚兜上秀五毒、在枕头、枕套上秀美丽的花鸟鱼虫时,别提有多神奇、多好看了!长毛兔也是我喜欢的,雪白的毛长的很快,柔软光滑,我还清楚地记得与妈妈配合,在院里的小石桌上给兔子剪毛的情景,以及小兔仔仔生下来还不会睁眼睛,竟然满地爬!只是,长毛兔繁殖太快了,我和妈妈照顾不过来,最终全送人了。
我压箱底的妈妈亲手用丝线在红绸上绣的中式枕面——
姐姐们也学到一些妈妈的针线功夫。下图是我儿子小时候,姐姐们给孩子在端午节做的小香包和孔雀灯——
我家里粮包一年比一年大了,再也不缺吃的,但五叔家那三个从小就没妈的大小伙依然吃不饱,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五叔不仅向我家借粮食,还时不时就去“云游”了,剩下三个小伙子在我家免费吃喝。妈妈说这几个堂哥可怜,从小没了娘,还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妹妹生下来就送人了,但那家父母有残疾,女孩子比在家的哥哥们更可怜。五叔是有文化的,早年是西北军政学院的学生,据说五十年代军队上生活好着呢,大白馒头和肉不限量的。可是后来五叔转业到地方上的单位,偏偏遇上载于史册的饥荒六零年!顿顿吃不饱,五叔太饿了,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就跑回家,打死也不去上班了。就这么的丢了工作,可是五叔对种地没兴趣,写写算算画画的事倒是总少不了他,比如村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他必定是坐在收礼台前的,一手小楷很了不得。五婶早逝之后,五叔就成天追赶庙会,不仅是居士,不知何时还学会了给村里人请神驱鬼呢。偏就是不好好种地,他家里全是男人,饭量大,当然吃不饱。想想也是,当年粮食不够吃的时候也周济他们,现在我们家粮仓鼓了,不怕给他们吃。
说到五叔了,不妨也提一下我爸兄弟中另一位听故事就让我刮目的人——我的二伯。二伯没成年就被抓了丁,后来逃回来却又被县保安大队给“请”了去,再后来,二伯就很威风地成了县保安大队长,骑高头大马巡逻,威风的很呢!听说迎娶二娘的时候,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是高头大马的骑兵,从家门口排到村外大马路上去很远。小时候二伯家跟我们家同住一个院子,我很少见二娘出来,经常盘腿坐在炕上,后背挺直,头发油光闪亮,一丝不乱。很少话,但说话时我们不敢不听。倒是二伯,去全然没有别人讲的那样的威风,反而是背手低头走路,沉默寡言,成天旱烟锅子不离手。据说,四九年解放大西北时,二伯被抓了俘虏,还差点被枪毙。是爷爷借了很多粮食为二伯赎回一条命,二伯的性情从此就变了。所以我小时候听村里人说二伯的故事时,根本就,没法想象他威风凛凛是什么样子。
扯远了,书归正传。我家粮仓满了,妈妈似乎天还是忙个不停。多少年里都是一家八口分睡西房的两间厢房,拥挤可想而知。大姐夫每次来家里还得借住别人家。八三年家里盖起了东房三间,妈妈特别开心,对哥哥弟弟说:以后,你们两兄弟每人一座房子,弟东哥西,西房三间是哥哥的,东房三间是弟弟的。哥哥那年15岁,其实距离结婚还太早。而妈妈却想得挺远。随后,妈妈给家里买了一台压面机,就安装在宽敞的东房里——估计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甚至难以想象,一台长达两三米、高一米多的压面机!不是电带的那种,而是全凭人力操作机械。可以给村里人提供办红白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招待客人一定要吃的哨子面用的面条!这可是个创举!妈妈是村里第一个买机器回来赚钱的人!不过,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卖力的力气活儿!手工拌面絮子,手动搅机器压面片、切面条!真不知道妈妈哪来那么大的气力,有时一晚上能给人家压一袋子面粉!压一斤面粉5分钱,后来涨到7分,实在是太费力气。遇上办大事,妈妈就请办事的人家派个人来专门搅机器(就像用碌辘打井水那样),妈妈还是要和面、拌面絮子,只收3分或5分钱一斤。就这样,村里还有人眼红,于是村里就有了第二台压面机。而买第二台压面机的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八婶!妈妈妯娌里面最年轻、且以伶牙俐齿著称的八婶!爸爸担心妯娌之间因为这个起矛盾,就劝妈妈把压面机转手,说:她八婶年轻有力气,买了压面机也好,正好让你不要那么下苦力了。妈妈说:压面机转手也可以,那我就买一台榨油机回来,油菜籽榨油之后的油渣,冬天我给牛拌干草当饲料,春天你正好用油渣给花施肥,给院子里的果树和房前屋后的其它树当肥料。再有多余的油渣,还能卖钱。爸爸说买榨油机好是好,但不用急。总之,家里的压面机很快就给处理掉了。
不过后来,妈妈终究没能买榨油机回来,据说是爸爸有机会给我们家申请农转非——也就是全家把户口转到县城里去,能吃上商品粮了!不知道妈妈是否乐意,我反正高兴坏了!85年那时候,谁不高兴当城里人啊!尤其,我不用干农活了,我要去城里读书了!又被村里的小伙伴羡慕到流口水!
我家老院子拆掉前海满树繁花的梨树——我去县城读书那年它才第一次开花
一九八五年的九月,是我人生的里程碑,我第一次离开妈妈,跟着爸爸去县城,成为县中心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因为爸爸说我在农村时没好好读书,让我复读了小学五年级,于是第二年我竟然轻轻松松就考上了以县名命名的重点初中。可是,唯一的缺憾就是妈妈一个人留守在农村老家——家里的庄家还没收完,牲口一时来不及处理,也舍不得处理。妈妈更舍不得离开这个家,离不开她生活了几乎是一辈子、也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亲手打造的这个家!我们当然也离不开妈妈,每个周末都回家里去,一家人齐聚了,热热闹闹就像过节。周日傍晚再带着妈妈蒸好的两篮子馒头返回县城。不过有一个周末看见妈妈揭开蒸锅的那一瞬间,忽然一手抚额头一手扶灶台,有点站立不稳的样子!我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说,就是有点头晕,闭一会儿眼睛就没事了。果然,一会儿妈妈就好了。
八六年春节,是我们一家人在农村最后一次过大年。闻不得膻味的爸爸,却把两头寄养在南山大姐夫爸妈家的两头羊都牵回来宰了。这羊,原本买来打算给生下来就没奶吃的弟弟补营养的,弟弟太瘦了!可是,我和妈妈实在没精力伺候,爸爸只好把羊寄养到亲家的羊群里去。如今乘过年牵回来宰了,炖羊肉汤,吃泡馍,叔叔伯伯们、堂哥堂姐们都来我家吃羊肉泡馍,院子里满满都是人,也满满都是过大年的氤氲香气。五叔和八叔最喜欢啃羊骨头,尤其是吸食羊腿骨的骨髓的滋滋声,犹在我耳边。年少的我们,在春节这样的日子里,那真叫一个开心和无忧无虑!那一年初二,姑娘们回娘家,又是一番热闹的高潮。那天,我们当警察的二舅舅也来了,最关键的舅舅带着照相机,给我们全家照了好几张相片。
全家第二张全家福(拍摄于1986年正月初二),有三个姐夫和两个外甥了!
那些年的农村,过年热闹的很,都说“小孩爱过年大人怕花钱”,但正月里花钱热闹的时候,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吝啬。从正月十二开始,从村里到乡里再到县城里,到处都在耍社火。我们一家人都去了现城看社火。正月十五不仅有社火、有打钢花、放烟花,还有灯会猜谜,那简直就是一年之中欢乐的最高潮!
正月十五晚上村里的习俗是要给先人坟头挂红色的“火罐灯笼”的。妈妈和爸爸十五下午就回村里去了,由于爸爸自行车不会带人,三十里路就和妈妈一起走回去的。妈妈带了菜食回去,爸爸又招呼在家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吃饭拉家常,一直到夜深才各自回家休息。想必妈妈忙了一整天已是太累!然而刚睡下,村子里忽然鸡飞狗跳的闹腾开了,爸妈赶紧起来看,好家伙,隔壁(与我家共用一堵后墙、房子背靠背那样的)七叔家的灶房着火了!浓烟滚滚!大约是谁家放烟花不小心引燃的吧。木头的房顶,再加上厨房周围全是柴火,一场大火再说难免了!最要命的是七叔两口子那时承包了一个山庄,家里只有四个孩子!爸爸出门喊人救火,妈妈跑过去叫七叔的几个孩子赶紧起床。然后就是一起打井水灭火了!也幸亏那晚上大家都睡得晚,所以救火还算及时。然而,妈妈一回到自家院子里就一头栽倒在地!爸爸怎么叫也叫不醒,扶又扶不起!只好再次跑出门去喊人帮忙!多灾多难的一夜啊!
妈妈脑溢血了!半夜三更叫乡上卫生所的大夫来说是看不了,又去乡上打电话叫爸爸单位的大卡车来村里接我妈妈去县城医院。我们兄妹几个知道妈妈病重时已是第二天中午——正月十六一般是开学的日子,爸爸不回来,我们没法交学费。后来姐姐过来说妈妈住院了,正在抢救!不让我们去医院看望。后来又转到市里面去做手术。八六年六月,我小学毕业时,妈妈已经可以让我扶着去院里的花坛边看花草了。妈妈说,等到九月份我上初中开学时,她一定能给我做饭了!可惜,那时候厨房烧煤用的鼓风机呜呜直响,妈妈听了脑袋疼,而且妈妈也离不开手里的拐棍。就在那一年我开始学做饭。第二年春天,县城里照例开农业交流大会,村里的人们一般到交流会上采购农具、机器啥的,逛累了就三五成群地来我家歇歇脚、喝杯水,跟妈妈拉拉家常啥的,还有亲近点的留下来吃饭。我就不高兴,爸爸带着他们学校的老师去外县观摩学习了,要好几天呢,做饭的事就全落在我头上。因为我放学回来才做饭,吃完还要刷锅洗碗,一天中午饭、晚饭两顿都有外人吃饭,可我还要上晚自习呢,上学都是跑步去的,时间太紧张了!第三天我就赌气晚饭没回家,下晚自习回到家,妈妈说她和弟弟在学校教工灶上买饭吃了,还给我买了一份,在厨房用开水温着呢。说罢,就主着拐棍去帮我端饭了。我没理妈妈,而是提起炉子上的一壶热水去几十米外爸爸的办公室里洗头发。谁知,这竟是永别!听弟弟说,妈妈把饭端过来之后说头晕的很,就自己坐到床边去,又躺下了。躺下之前让正在写作业弟弟赶紧喊人,说自己不行了!
那一晚,我恨不得自己一头撞死算了!因为妈妈脑溢血复发的前一刻我还在生妈妈的气,埋怨妈妈留那些村里的人在家吃饭,不仅我累,她连续几天白天都没法子休息嘛!
爸爸那夜连夜赶回家!但是,回天无力!医院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而且放弃治疗。我们把妈妈拉回了她最心爱的农村老家。
妈妈就这样走完了自己50岁的一生,留给我们兄弟姐妹无尽的遗憾、无尽的思念和回忆!前几年给妈妈立墓碑时,哥哥在碑的背面刻下四个大字:恩深似海!每每念及妈妈辛劳的一生,却不曾享儿女们一天的清福,我们总是忍不住泪水满眶!
我曾在清明节写的一首纪念母亲的小诗,背景是老家院子里的梨花——
母亲节到了,今年母亲去世整整三十年,谨以此篇回忆录怀念我的母亲!
|